蒼鷺與少年(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中的隱喻主題
近日看完宮崎駿(みやざき はやお)執導的蒼鷺與少年,趁著劇情還記憶猶新,將個人對於本片隱喻的哲學主題進行簡單歸納,並簡單分析標題的日文,由於書寫本文時未參考導演相關訪問,純屬個人對劇情的詮釋,僅供參考。另外先提醒讀者,本篇有多重劇情劇透,若會介意不建議未看過本部動畫和鈴牙之旅的人觀看。
標題「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解析
在台灣和歐美地區,本片上映的標題為「蒼鷺與少年」(The Boy and the Heron),中國地區則較保留日文的原題翻譯「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若採取直譯則可譯成「你們想要如何活(著)?」或「你們想要如何過人生?」,逐字分析標題如下:
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
你們 主題助詞(點出句子主題) 如何(修飾後方動詞) 生活/過活(原形表意志,未完成,非過去式) 疑問助詞(表示疑問語氣)
「蒼鷺與少年」點出本片兩個主角,卻無法看出劇情,帶給觀眾一些神祕感;而日文原題則直接破題點出本片探討的主題,但容易讓觀眾有本片較為艱澀先入為主的觀念,但確實很契合本片內容,就是去尋找接下來生活的方式,為何選擇這樣的生活?生活為了什麼?生活有意義嗎?如果有意義的話是什麼;如果沒意義人生,那麼活下去又是為了什麼?宮崎駿不是第一次用「生きる(活,原形)」這個單字;在魔法公主(もののけ姫)時,宮崎駿就以採用「生きろ(活下去吧,命令型)」當作電影標語,在當時歷經泡沫經濟、大地震、沙林毒氣事件後的日本引起廣大的社會反響。
主角的名字真人(まひと)解析
「眞人(まひと)」作為一個日文名字(導演刻意選擇了舊字「眞」,而不是新字體「真」),向觀眾點出意思就是:「率真誠實的人」,也有可能借用了道家思想,表示「了解真理的人」,和現代中文意思不同,白話中文一般語境下的「真人」與「假人」相對,意思既不是機器人或人偶之類的假人。和主題呼應,整部片就是男主角真人變為誠實的過程,從踏上奇幻旅程前的不誠實,到最後向曾祖父坦承傷疤為自身的惡意;從用仇恨欺騙麻痺自己,來轉移喪母的悲傷,到最後有勇氣重新回到現實世界,整個旅程是男主角逐漸去除自身的虛偽、不誠實,回到現實的過程。
塔中世界和鳥類的隱喻
時空走廊的隱喻
如何看待死亡與死後世界
身上的傷疤就是惡意的證明
真人兩次拒絕建造理想國即本部片設定中理想的塔中世界,第一次是他發現所謂用於建造祖父喜歡世界的石頭,是建造墓碑的石頭,這樣隱喻指出石頭是帶有人類惡意的;第二次當祖父從其他世界找來了純白無瑕的積木石頭時,主角仍然拒絕建造他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因為他看到了他當時帶著仇恨、絕望,而故意用石頭去撞擊頭的傷口,也許這個傷口是為了要製造繼母夏子的罪惡感讓繼母擔心;也許是為了發洩情緒而自暴自棄的舉動,不論如何,這都是他心中有惡意的證明,因此他再次拒絕,並解釋道他若觸碰這塊石頭,同樣身上的惡意也會汙染這顆石頭。這段情節強調了每個人都有惡意,或者用更宗教的術語來說:都有罪惡,雖然這不是整部片探討的主題,宮崎駿也沒有展開論述,人是天生性惡嗎?,又或者人如何看待、解決自己罪惡與惡意的問題,但還是一段不錯的橋段,點出人的不完美。
這一段劇情又讓我想到浮士德中的情節,人類永遠不可能建造成功理想國,即使理想國的心中願景再美好,因著人的罪惡,在建造時採用了暴力、流血、奴役,又或者參雜了任何一丁點惡意,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理想國,因為本身就被汙染了。再理想的目標也有可能變成惡意的工具,理想國就像「烏托邦」一詞的雙關,真實世界是無法存在,靠人手打造的必然有惡意,如同許多反烏托邦小說的劇情的反思,要完全杜絕身體不完美,就得透過基因改造和優生控制,這樣的完美是我們要的嗎?或者這樣真的就是完美了嗎?還是更容易造成精神的殘缺?;要杜絕犯罪就得使用全面監視的系統,但這樣就根除了人心中的惡嗎?是否也會有誤判呢?人常常為了理想的目的而不自覺得離惡越來越靠近。因此在這裡,真人拒絕建造積木,另一個他內心裡想的世界十分有智慧。
脫離虛擬,回到現實世界
整部動畫花了很多篇幅,描述男主角都穿越到曾祖父塔中建構的虛擬世界,並替神秘的高塔鋪下許多伏筆,最後揭開這個虛擬世界的神秘面紗,就像沒疊好的積木塔一樣不穩定隨時會倒塌;而在結局男主角勇於拒絕曾祖父的要求,不再建構虛擬世界,鸚鵡國王憤而代替他疊積木塔卻失敗,積木塔倒塌伴隨著世界崩塌作為祖父在塔中建構虛擬世界的結局,這段劇情也讓我不禁想到,諾蘭在「全面啟動」中傳達的同樣思想,和「駭客任務」,也就是不要在待在虛假的世界裡,回到現實去承擔應有的責任,因為責任和現實是不可能永遠逃避的,人們害怕責任是因為害怕選擇,但正如沙特所說,不選擇何嘗不是一種選擇呢?
所有這類型描述虛擬世界的題材,其實主旨都是相同的,不是要我們總是疑神疑鬼,這個世界是否全部都是假的?而是讓人審視自己的生活是否有中心,還是渾渾噩噩,因為不見得要等到全人類都如科幻電影進入電腦世界之中,或踏入虛擬世界才要思考我們的世界是不是真實的,若我們的生活沒有中心目標和信仰,不清楚自己為何這樣過活,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該做什麼?那麼我們就是行屍走肉,跟活在虛擬的世界一樣。
親情作為生活和選擇的意義
本片最後劇情動人的高潮在於真人(まひと)的母親久子(ヒサコ),年輕時尚未成為真人母親的火美(ヒミ),下決心仍要回到那個她會在醫院死亡的世界線,因為她仍選擇要成為真人的母親,並珍視與真人的親情,將之視為自己生活的意義,甚至勝過生活的意義,所以她不對死亡和這段人生感到恐懼。這裡引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生命是為何而活?哲學對於生命和生活的意義有幾種解答,有人認為是親情、友情或愛情各樣人際關係,人就是在社會中獲得意義,有的說使命、信仰、上帝、追求真理,透過尋找上帝賦予自己的使命、信仰得到真理與意義;或對於無神論者來說:透過天分才能或追求自然科學的規律來找到意義,也有像尼采和卡謬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覺得生命是荒謬的沒有意義,但只要認真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過活,不須度光陰,就不算虛度自己的生命。
如漢學家萬百里所說,相較於將意義訴諸於宗教(使命、信仰、上帝)、追求真理、政治等地西方哲學來說;東方哲學,尤其是儒家思想,更重視親情倫理作為生活的意義,宮崎駿同樣將本片探索意義的解答以親情作結,如同和本片幾乎同時上映的「鈴芽之旅」最後當女主角再次進入常世(死後世界)後,穿越時空鼓勵小時候的自己,即使母親死去,依然會遇到很多愛她的人,她也將會與阿姨一同生活,並肯定已經找到自己的幸福,同樣是以親情作為生活的意義作結。
知道未來會怎樣,我們仍會去做那樣的選擇嗎?或許這是人類看不到未來的原因,是否很多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知道結局不好就沒有勇氣去做了呢?異星入境的女主角,也知道女兒會死去,但仍選擇生下女兒,因為即便知道有可能有悲慘的結局,她仍將此段記憶視為他生命中重要的意義,雖然這也讓她先生害怕顯得他似乎很沒人性,在這裡宮崎駿則顛倒了角色,假設母親自身之到自己會死,仍會選擇進入這個世界,再次讓我們思考人生中有哪件事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達成的?即使結局未必完美也要選擇去做。
本片的一些未解問題
本片較可惜的點是仍沒有交代清楚死後的世界和生死觀,即使前方花了很長的時間鋪陳,最後,主要的場景和冒險,仍是發生在塔中的虛擬世界,死亡世界以含糊的方式帶過,蒼鷺告訴真人母親沒有死,還在某個地方活著,也許這是雙關語,一方面是指這個塔連接著各個時空,而且塔中世界的時間也與外界不同,因此,真人此刻進去仍能看到尚未死去的母親。
或許還有另一層意思,在宮崎駿和真人的眼裡,最後他們能釋懷,也是相信死後世界就存在於某個地方,本片中時空走廊,尚有多扇門沒有被打開,也許有扇門就是通往死後的世界。這也是為何死後世界是許多宗教關注的核心,每個宗教都對死亡後有不同的描寫,並對於怎麼去到更好的世界有不同的,因為這是人類的基本問題之一,「我們該往何處去」;也或許宮崎駿是刻意避開死後世界和靈魂的描寫,他有可能抱持著和尼采類似的看法,認為好的哲學和作品,要更關注「活著」,而不是「死亡」,如同《論語》寫的:「焉知生,未知死」,畢竟藝術文學作品,我也不要求作者清楚描繪他的生死觀,但還是認為本片總覺得缺少了些什麼。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從主角母親美紀的角度來看,親情雖可作為生活的意義,也可以帶給人希望,但是男主角真人不也是因為過於看中死去的母親而難以釋懷嗎?難道他真的因為本次與年少母親相見的奇幻之旅就能完全撫平傷痛嗎?我們也可以反思,另外如果將親情當成唯一生活的意義,那麼天生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又或者喪失摯愛親人的人又該如何做呢?所以我認為,無論是何種情感或愛,仍然不應該充當所有生活的重心,我們仍要去認識自己的自我,去尋找自己生活的信仰,去嘗試尋找真理,去找到自己要完成的責任與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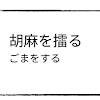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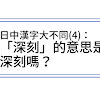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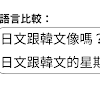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
感謝您的留言與支持,我將定期回覆!